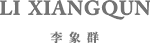李象群进入了当代艺术领军者的行列,故宫个人展是最后的宣言,或者标识一条道路已经形成。中国的当代艺术的格局在过去的30年里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局,学院和江湖、体制与民间的性质互相逆转,这个变局在于学院成为当代艺术的人才、理念和创作展览的基地,而30年来当代艺术界已经逐步形成对资本和权力紧密依傍的江湖,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自律松弛,有时比学院体制采用更多的操纵和权术,而且缺乏监管机制。
根据“中国现代艺术档案”(CMAA)1986年以来持续的观察、记录和分析、研究,2010年以后,中国当代艺术发生日益明显的分化。首先是原来作为反对和排斥当代艺术的学院系统转变立场,接受并推进当代艺术,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天津美院、西安美院、鲁迅美院和其他几大美院的主要领导以身作则,亲自参与创作并有节制、有技巧地推进当代艺术的观念,并将之引入教学;而文化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国家画院也建立了相应的当代艺术机构,研究和介入当代艺术;中国美协有限度地成立了当代艺术的组织与指导机构“实验艺术委员会”,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以“实验艺术”的名义设立当代艺术的专门展区,使得整个中国的公共媒体和展览教育机构在封闭二十多年后完全向当代艺术开放;教育部以实验艺术的名义设立了当代艺术专业,探索性地在全国各个院校展开当代艺术的教学,当代艺术逐步回到了基础教程和素质教育的正常地位,取得了全面的合法地位!而十年苏世独立、同气相求的“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旗帜鲜明地以民间(非政府、体制外)的立场推动当代艺术,也积极筹办当代艺术学院,把教育和对理论的系统研究向前推展,却又向学院系统逼近。如此一来,使得原处于紧张而冲突的两个方面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而这个现象正好与当代艺术界的一些现象相互对应转化。有些已经出名的当代艺术家创造力退化,对现代批判精神疏离,他们叛变了当代艺术的底线所要求的独立人格和民主精神,以操纵权术和生意兴隆标榜。有些过去以探索新技术,利用“实验艺术”和“当代艺术”出道的成名艺术家在精神上发生了根本的变质,逐渐把自己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样式变成了一个品牌和风格,从而成为一种经典,成为一种新的传统,他们对这样的传统的维护、保持,甚至操纵舆论,虚造文献档案,购买对自我的评价,已经到了不遗余力的地步,甚至构成了一种霸权,这种霸权是商业公司的套路,政治利益的联盟,加上以“艺术”之名所获得的“特权”——利用无节制的编造(美其名曰“创作”)和不守规则(美其名曰“性情随意”的“自由”),使其轻易获得名声和财富的迅速积累。也就是说,过去与学院艺术对立而具备专有性质的所谓的“当代艺术界”已经分崩离析,变成利益公司、保守和专制势力的滋生地,其精明和虚伪的程度,完全与当代艺术秉持的政治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背道而驰。这种情况甚至发生在试图操纵学术研究和专业写作的领域,遇有不符合自己的意见和己所期待的言论的时候,有一个艺术家竟扬言要求有多一点权力,采取“杀无赦”的镇压办法,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攻击侮辱和废除,充分暴露了其内心已经滑暴力和专制。在市场经济越来越具有重大影响并主导地位分层的社会,创造稀缺而珍贵的精神产品的当代艺术,成为财富追逐的目标和金融运作的载体,本来不可避免。但是,如果作为当代艺术的创作者放弃了批判和拒斥的位格,主动参与并且无限利用资本和权力炒作,这是一种当代艺术的中国式腐败。
当代艺术近十多年来毕竟还是取得重大的发展,只是当代艺术原来作为一个理念和方法,与学院艺术(西方传统艺术)和传统艺术(中国传统艺术)三足鼎立的界限分明的区别已经模糊,尤其是2010年以来的一系列变更之后,已经出现了三个方向。其中,第三个方向就是反对当代艺术的江湖和过分商业化,发奋自我更新,在学院中反而将理想主义和青年(学生)思潮转化为更多的社会质疑、现实批判和文化超越的纯粹意义和文化担当。
变更后的第一个方向是内容上的批判意识和独立意志。在这一点上,几个效果显著的艺术家在世界范围之内,把中国政府的形势和状况作为一个针对目标,作品激发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冲突和广泛争论。这种直切现实矛盾的形式,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中,价值判断被现代媒体和互联网迅速传播,受到了国际上持不同意识形态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阶层的普遍关注,这是中国近自有当代艺术以来所不曾遇到过的情况。
第二个方向是新媒介。上述艺术家个体的艺术作品的“内容”得自于媒体时代和机械摄制技术的新媒介的传播功能,但是新媒介远远超过传播功能,其主要意义在于改变人的感觉的能力,同时改变世界的性质——用虚拟“形相”取代“物质世界”,等于是给人机会用创造置换“真理”,其深刻程度,远远超出了现代权术和国际政治的范畴。这个方向并不是由艺术家独自占取,虽然有很多艺术家介入从事,但是中国的新媒体教育已经突破了艺术的范畴。对世界现实和人情世故的了解、把握、表达和交流是通过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使用来实现的,而新媒体和新技术的随时更新,给所有人带来巨大的可能性,使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同时面临前沿,处在同一队列,每个地区和集团都在探索和创新产生突破未来的方法。在这种形势的逼迫下,像电影这样兴盛的媒介正在成为一个过时的、多余的夕照,更新的媒体每天都在发明和诞生,当代艺术由此发生突变。
而第三个方向,就是李象群所代表的中国当代艺术:学院向当代艺术转化之现象,即通过学院常用的“美术”这种技术本身(此处的“美术”,用其法文beaux-arts的原意,是指“为艺术而艺术”,使艺术成为经典的那种美术),来对应媒体时代和机械摄制技术所带来的“人的异化”,从而对当代人的审美意识和感觉习惯进行干预。当代人的审美意识和感觉习惯被不断更新的媒介所引导,已经使人处在失却实在感的恍惚之中,需要调用人类自古以来在艺术品中保留的那种贯穿的感觉,把人从图像和视觉的虚妄状态中拉回到实在,这个方向绝不是表面上回到学院,复兴学院原有艺术的范畴、理念和作法,好在李象群完全清楚!而且自觉地做出了清晰明确的区分和选择。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学院,而不是学院外,本来才是容易成为产生新人(学生)和新见的地方。中国的当代艺术从事者,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理论家、批评家,很大一部分都出自于学院,一些所谓“社会上的”(非体制内的)艺术家,不少人也是经历了学院的训练,获得成为艺术家的(值得怀疑的)基本技能和系统知识以后才进入当代艺术。而很多成功的当代艺术家保留着学院的教职,没有教职者也受到各个学院的尊崇和吸引,已经或者迟早会与学院发生瓜葛。那么这个情况就带来了一个矛盾,到底是反对“学院派”和学院体制,还是潜入学院以“改造”学院?这个问题对于学院中人来说一直是一个纠结,也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即如何用学院的方法发展出新的当代艺术?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彻底的超越和摆脱,向前推进,不仅与西方的当代艺术一起越过学院,而且越过西方的当代艺术,用过去没有的新技术、新媒介,探索全新的理念和艺术;另一种是对从西方引进但在其故乡已经疏离的古老的学院方法和技术进行一次现代性改造。许多从学院出身的艺术家,既有对未来发展的清醒认识,知道只有当代艺术将会被后世写进艺术史,同时也有一种跟自己的心灵、心理和学识修养相关联的习惯方式,他们试图利用自身的学院基础直接插入当代艺术前沿的努力,造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一股特殊力量,这在学院的故乡西方反而没有。
过去从西方引入的美术学院所教授的传统艺术是一个混合体,其中有西方艺术的经典方式,也有写实主义技术和现实主义观念。
经典方式渊源于两千年前(从希腊公元前5世纪古典时期开始)的(造型)形式的典范。这种积累下来的形式是一整套从具体的内容和技术之上提取出来的规则和理念,凝聚着永恒的人与创造和感觉之间的普遍关系,穿越时间,可以触及和激发各个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的个人的共通的感觉和体验。这种超时代、超文化的感觉和体验源于经典形式,而对这种经典形式的反应通贯于许多或所有个体的生理和心理深处,此即成为经典艺术成其为“经典”的根本。
西方艺术学院教授的传统艺术里面还包含历史上获得重大成就和发达的写实主义技术和现实主义观念,然而,艺术作为记录(现象和形象)和叙事(对世界和事件的陈述和描绘)的这种方法已经被现代媒体和机械摄制技术所替代,才促使西方学院艺术决然在自己创始、发展和到达完美极致的地方完结了历史使命,开始了自我革命。
当代艺术的第三个方向,正是在写实艺术已经被新媒体、新观念、新技术所突破、取消之后,在图像媒体时代到来之后所出现的另一种新艺术,这种新艺术是把学院艺术中的经典要素作为留住人的“历史本性”的方法,使人们不至于在虚拟世界和信息时代被媒体彻底异化,维护和保持人和现实之间的联系,借助经典艺术品在任何时代都能被所有的人反应这样一种“永恒的特性”,唤醒和加强人类自身的情性和感觉,连接文化记忆,保护人对自己的遭遇还具有符合其作为生物的生命个体的感觉和自尊,从而把人的本性留住,不被信息和图像覆盖和淹没。
“学院”从上世纪初引入中国,本来是为了打破艺术的旧传统而进行的“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是反对艺术上秉持经学和国学的传统的一次颠覆和革命。时过境迁,今天看起来,当时的做法和想法未免偏激和急切,但在中国现代化初期,学院曾经是一个积极而反叛的力量,是我们国家救亡图存,反对压迫,摆脱落后,走向现代化的意识和力量。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变局,这种“创新”事物由于时代局限(意识形态和发展阶段的总和),很快在引入不到100年,其改造和更新的势头逐渐和缓并消失,难于与时俱进,成为艺术中保守、限制和统治的力量,逐步变成了中国进一步思想解放和文化创新、发展的阻力,至少不再能够承当中国继续现代化,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先锋角色,所以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现的新的艺术成分,不再是100年前从西方引进的学院艺术,而是反对学院的当代艺术。而在学院内部,自我改革的力量从未放弃过对于当代艺术的努力和探索。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向世界和历史展示,现代化是使中国强大和发展的道路。难道艺术可以是一个例外?今天中国文艺政策虽然开放,提倡西方、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各种艺术观念和创作方法,反对追逐铜臭,贩毒低俗,但是美术权威系统还多少停留在随美术学院引入的西方写实和现实主义观念,对当代艺术的成绩,只是刚刚开始正面的肯定。但是,也许再过若干年,人们才会意识到,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崛起,高速的发展,物质成就有目共睹,而其潜在的精神实质就是在当代艺术中得以反应和反射的,因为艺术反映的是社会思潮和心理状态,这些是不能呈现于事物的表面,用写实和现实的记录和描述难于充分展现。而反过来,如果没有中国的当代艺术(当时一开始称作“现代艺术”强调其属性,现在称为“实验艺术”强调其方法)的参与和促进,中国改革开放要取得现有成绩也不完全。这里并不是夸张当代艺术的作用,而是在揭示现代化实质的意义。如果现代化的结果只是增加了物质的丰富性和社会财富,那么,我们就过分小看了现代化对于人类文明和一个国家真正的价值所在,即对人的基本权利和精神素质的深刻影响之所在,艺术只不过是后果的显现,也是一种(作为创造原因的)动力。在国家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艺术不可能保持在原有传统的、经典的、保守的学院里,虽然社会和市场需要宣传和装饰的文工队和手艺人,但是文明更需要艺术的开拓和引领。艺术学院不仅多少会受到现代化的影响而出现实验和反叛的局部活动,而且,艺术本身正被要求成为现代化的动力,成为创意的素质和发动,成为现代社会积极推进的因素和最有创造性的力量。
在学院的整体制度和结构的状态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曾经以传统艺术为主要对象如油画、雕塑、版画(国画另有专论,此处从略)的许多教师和学生,与新媒体、多媒体、跨媒体等实验艺术和现代艺术专业人员一起,部分人自觉地走上了当代艺术的道路。学院中的当代艺术的道路上也有两种人。一种是身在学院,却完全不按照艺术学院的方式进行创作的人,他们的观念和方法与任何一个不在学院内的当代艺术家没有两样,只不过他们身在学院而已,这部分人其实构成当代艺术界的主要成分。第二种人就是继续使用学院的根基和技巧作为进入当代艺术的方式。李象群作为第二种人的代表,在引领这一当代艺术的实践和实验的过程中,,必须首先面对两个问题,一个是当代艺术反学院的性质如何在学院中成立;第二个是如何把学院方向的当代艺术与复古的、时尚的、外行高价收买和高度评价的那种媚俗的行画相区分。
李象群的同人在学院里面实际上相当纠结,这种纠结凝聚了当代艺术和学院艺术的冲突,自己从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些修养和基础,在当代艺术中基本甚至完全不在艺术价值的评价体系之内,与现在的艺术评论和未来的艺术史写作几乎没有关联。其警示就是卢浮宫现象,卢浮宫中收藏的作品是中国学院望尘莫及的榜样,但是在其祖国,在诞生它的西方,没有一位当代艺术家使用卢浮宫里的观念和方法作画。卢浮宫已经形成的艺术史截止于1840年之前,但是照着卢浮宫的方法,再也无法被写进后来的艺术史。在国内有些技巧精湛的学院作品虽然今天的价格高,也获得群众的认可和官方的认定,但是想要进入艺术史就不够,有此雄心者不可能不把自己开向当代艺术。然而当代艺术对于学院的否定,成为对他们自身的经验、品味以及自我尊严和地位的否定。在西方,由于艺术家们都已经远离卢浮宫,对此情况并不纠结。而在中国,类似卢浮宫的学院方法至今仍能使人获得政治地位和经济状态的极大成功,因此就不可能不纠结,于是逼出一条生路,就是要重新把经典中的一个因素单独提取出来,使之变成具有对抗图像和媒体时代的一种鲜明的力量,突入到绝学中求得超越,在学院这条道路的尽头,化生为当代艺术。
做着这种方向努力的艺术家是分裂的,这种情况很容易被外行看成是对古典方式的恢复,其实性质完全不同。李象群的成绩已经是致力于当代艺术深入实验,却被外行和群众(中国大多数收藏家)当做传统艺术家接受。中国批评界众说纷纭,不被批评界质疑和监督,而被批评界两面接受,雅俗共赏,这正是这个艺术家性质模糊,未来最终进不了艺术史的障碍之所在,世俗路途宽广,艺术的任务却艰难。
走在这条大路上,作为最重要的代表李象群,其艺术实际上坚持着这样一个方向,就是用雕塑的技巧去塑造情绪充满的肉身,以古典含蓄的手工塑造的形体,诱惑观者进入被题材和物象所迷恋的状态中,然而沿着这个状态再向前一步,任何简明的政治意义被自我否定和自我抵消所阻断,进入观众内心的是一个悬置的“经典”本身,经由形体而输送到人的感觉之间。这种手法曾经发生在古典晚期,罗马雕塑失却和废除了希腊雕塑中的神性(意义),而仅仅保留对经典形式的欣赏和凝视,这种损失曾经被说成是古典精神的衰弱颓唐,其实正是人的“情性”对规范的挣脱和超越。当年罗马雕塑家从道德上如何看待自己对希腊古典神像的遗神取貌的背离,实在难于忖度,但是当抽象的经典形式脱离了当时当场的意义被独立欣赏和运用时,个人的自由摆脱了时空和体制,摆脱了利益算计和理性评价而进入与人类沟通的直接状态,感受,就能被觉察、意识,却无以用语言表达,因而穿透了被时代和权力所规定的话语,无限制地流通在人之间,跨过时代和文化,得以“永恒”。
李象群的艺术因而就不能归入一般性的当代艺术的概念,而是开拓了一个新的可能性,既是他的境遇所指,也是他的义务必须承当。学院经典可以被抽取、单独使用并介入当代艺术的路径很多,他的极度精细和敏感的雕塑手法即是对当代性的一种探索,跨越意义,穿越当下,穿透现实对人的巨大的限制和压抑。在学院制度还是唯一教育系统的中国,在学院中做这样的工作,还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但目前讨论的李象群的艺术,已经不是一个让人来谈论的理论方向,而是他几十年一贯的创作所产生且必须进行研究的艺术成果,而这个研究并不是因为故宫的个人展览才临时进行,而是一个长期的与从世界文明的各种角度进行研究的初步积累,检验和证明李象群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为一个“艺术史中的艺术家”。
对李象群在这个方面的实验已经有过一些研究。四年前国际艺术史学会的三位专家来到北京,共同开展了李象群研究,同时通过多次调查、交谈和参观展览、艺术家工作室,已经形成初步成果,并在北京大学建立了李象群艺术档案。
佛罗伦萨的艺术史学院院长Gehard Wolf教授的研究主要是从李象群的艺术中发现了一个文艺复兴艺术的共通要点,就是借对权威的肖像的处理来表达社会观念意识的变迁。这个研究表达了一种对当代肖像的创作角度,即并不展现对象的全部特征和背景,以及此人的特殊的生理状况和心理状态,而是由艺术家超越对象,制作形象,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评价。从文艺复兴时代对肖像的理解来看,尤其是死者的陵墓雕刻,其实都不是给当时的人看的,而是给后来的人看的,后来的人不会在意这个人当时实际是什么样,更注意的是今天“应该”什么样,或者作者所在的那个时代是怎么去看待和评价。这是一种学院艺术的方法,一种制造历史的虚拟真实的方式和技术,历史人物经过这种肖像处理,让人一惊,恍惚中间似乎忘乎对象本身。这种技术是从文艺复兴时代发展起来的,尤其在雕塑方面更是如此,而这正是李象群方法运用之所在。
美国艺术史学会主席Frederick Asher教授是从与印度雕刻的对比来进行李象群的研究。其问题指向肉身与神圣的关系问题。在印度的雕塑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试探,即把神圣体验的意味和生命中情欲激越的表达与放纵融合于一体,雕塑中呈现出一种张狂和沉迷的状态,形成了对觉悟瞬间的视觉凝结。通过身体的塑造,用一种肉身的感觉来突破教条的枯寂内容,从而产生抵消对立、消除限制的超越感。这种超越的感觉使得艺术家创造了一种可能性,他用这种技术去除了意义内容的僵硬性,而在这样的一次交融中,个人的历史批判力量突然被自由地释放出来,人的价值返归人的肉身。
第三个研究来自当时的墨西哥艺术史学会主席Peter Krieger。他的研究从墨西哥的艺术对比观察进入,墨西哥的艺术有两层意味,一层是发自于古代的玛雅文化,曾经将人的生命和血液与热带雨林进行神秘的自然搅拌,把活人的献祭变成对于土地肥沃、粮食丰收的牺牲,而这种奉献和牺牲的承托,使得作为背景的“雕塑”和“建筑”、置放坛场(也就相当于当代艺术理解的空间装置)具有直诉观者之生理激动和心理惶然的功用。在这些功用随着玛雅文明的断裂而消失之后,雕塑和建筑作为现代人的“艺术品”,展览的两大主题人体与建筑发生了关联,古代的肉身与废弃的宫室在雕塑中共同变成一个整体,故宫作为人性牺牲的政治坛场的意味被提示出来。李象群原来的艺术中似乎缺乏人与建筑(人体与故宫)的关联理论,通过Krieger教授的分析,这个方面获得了一种弥补和展开。Krieger教授对李象群的艺术还做了另外一个层次的推进,那就是图像政治学方面的推进,这是教授对墨西哥当代艺术方法论研究的重点之所在。因为李象群的作品从来就不是把一个人物放在一个历史单纯的孤立状态或者一个现实装饰和娱乐的广场上来观看的,而是放在一个真实的政治环境中,这个真实的环境就是一个肉身遭遇秩序的压抑及其对之进行的反抗。Krieger将这两个问题的层次和李象群的艺术分析结合了起来。
故宫的展览终于呈现出这个肉身与坛场之间紧密纠缠的状态,学院练就的经典雕塑技术衬托金碧辉煌的建福宫的轴线,穿透到尚未修缮的院落,历史中的人物从美轮美奂,到怅恨深长。故宫作为博物馆保存了旧社会对人性进行规制和载控的权力场,一道一道的门洞开,让当代艺术的实验得以实施,一道道门打开到了尽头是一个宝座,那里本来有一堆云一堆雪。《堆云堆雪》是李象群完成学院艺术向当代艺术转换的标志性作品,两个似乎从深宫的权力核心剥离出来的肉身,一曲用唯美化解政治的歌曲,不曾存在,却魂在此间。然而故宫的特殊规定不能陈列,展出的核心只是一个空置的计划,变为凌空的空白,一如故宫院长所说,天气还太冷?
如何来继续研究李象群?这个问题也可以追问:中国的艺术学院如何转型?如何进入当代,成为现代化的先锋聚集和文化创造的核心基地?李象群艺术性质的变化不是他个人的努力,而是代表着一个潜在的飞跃。当代艺术和学院艺术之间的关系发生转移只是现象,实际上背后存在着更为重大的问题,那就是艺术学院这样一个培养和造就人才的地方,将要为国家、民族和正在到来的图像与信息时代培养什么样的人?进行什么样的教学?承担什么样的社会作用?
朱青生
2016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