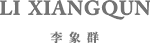李象群:我的十个雕塑关键词
•1喜欢•2北京•3 798•4《堆云堆雪》•5《孔子》•6《山丹丹花开红艳艳》•7《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8莫唯•少女•女孩•9紫禁城•10如何传承和如何当代
1、 喜欢
想起来,我对于画画的喜欢纯粹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欢,无来由地就是喜欢而已。没有人鼓励你,也不会有人来有心点拨或者来教你,就是有那样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发的画画的欲望。它更像是我自己钟情的一种游戏,能让我沉迷和陶醉在其中,浑然忘记身边身外的人和事。
从小,我就是一个特别安静的性格,不太和别人搭腔说话。有一个印象,就是家里人说话、喝茶或者打牌的时候,我就会钻在桌子底下,玩一些我自己认为特别好玩的东西。比如拿跳棋当人,拿一些器物当我所要表现的东西。在那个世界里,完全就是想象,而我自己却是深信不疑地当着真的。
我还记得幼儿园的时候,就喜欢画,就是在地上画毛泽东的像。有一回,差一点惹来麻烦。家里人就告诉我不要再画了。父亲完全是一个作政务的公务人员,喜欢在他的笔记本来画一个松枝,一架小飞机,间或是开会的场面。他只是喜欢而已。我每每看到,就是特别喜欢的感觉。还有,叔叔大概是在文革期间,用胶和木屑,染上颜色,拼贴毛泽东像,我就觉得这么好看呵。有很深的印象。
文革的时候,没有家了,我和姥姥住。开始的时候还拿纸牌来玩,那上面都是水浒的插图,特别漂亮。我就看着里面的人,让他们打。后来因为纸牌也沾着封建的边,被收起来了,不能玩了。我就开始自己粘纸条,粘很长,就在上面画,自己编故事来画。印象中有一阵特别喜欢画摩托,而且还是正面的带挎子的摩托,上面坐个老红军,络腮胡子,腰里别着枪。看的人都说这哪跟哪呵。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孩子的形象逻辑,没什么道理,却也挺有意思的。
说起来,我是特别喜欢画画,到处问人要笔要纸要颜色来画画。从小到大,就是喜欢画。看小人书,会在书边上画。书桌上我也画。课本上就更别说了。我的课本被老师拎出来示众批评过好几次。我学画也算比较早的。十来岁左右去文化馆学画,穿着脚划子,背着画夹,一路驰过,去到太阳岛那边。刚开始学,先分到的乙班二,什么也不懂。第一次画贝多芬的切面像,就想那么直,我画不了那么直,怎么办,我就用尺子来画。那张画因为放在一个吊铺上,无意中还留着。当时真是很有意思。老师说要用你的手来表达,不能依靠工具。现在再想,其实尺也有尺的办法。没用两年时间,折腾了三期画班之后,我也迅速升级,进了创作班。
的确,从小到大,只要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就特别相信我一定能做好,想来也是画画让我有这样一个自信的人生态度。再说雕塑,小时候用雪捏雪人,后来也用泥捏过,还是因为那部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当时就觉得雕塑家做得太棒了,虽然当时也感觉雕得和本人并不是很像,但就觉得特别有力量,那也是雕塑最初给我的一个震撼,感觉一直都在。
2、 北京
我研究生的时候就想上央美(中央美术学院),鲁美(鲁迅美术学院)的老师希望我在本校继续深造。我当时就想,在哪里上学其实都无所谓,但是我的最终目标是要到北京的。研究生毕业那年的九月份,我把我的小册子拿到央美。他们就问我鲁美会放你吗?只要你愿意来,我们就不惜代价去申请指标。我说我肯定愿意来,他们说“你要有这个决心。我们就尽力去办。”这之后,他们有给鲁美写信,说是“希望鲁美以大局为重。”
我来北京之前,我的老师对我说“北京是一片汪洋大海,我担心你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就被淹没了。”而我当时的心态,就是我年轻呵,我愿意去拼一次。我要是被淹没了,输了,我就认,是我自身能力不足。但我得要服呵,所以我一定要下水去试,我要是淹不死呢,我就会站起来,站起来我就会比原来更有力量。这也是我之所以选择来北京,进美院,特别重要的一点。
我始终都是做什么事情,都不要给自己留后路的那一种心态。我自顾自得往自己认定的前路方向,一路向前,凭的还是不肯停在原处的一股劲头。包括从央美出来,就是因为我感觉到对我个人想坚持的教学思想体系的发展不利。的确,每个学院都有自身所认定和认可的教学思想体系,有的思想体系是你个人根本改变不了的,于是,你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我不适合为官,只是喜欢教学,这和我的创作是并行不悖的。教学需要靠理论,作品创作是实践,二者相长。我也是特别热心教学的一个人,当我感觉到无法传承自己教学思想体系的时候,就觉得那是一种耽误。尽管美院给了我个人很大的认可。文革之后,央美第一次评正高职称,我们这茬77级以来的人中间,一共评上了四个人。我是满票通过的,而且还是最年轻的,三十七岁,可谓是破天荒了。其中的一个缘由,当然也是因为在这期间我连续拿了两次雕塑金奖,一件是《永恒的运转》,一件是《接力》,这也是我自己没想到的获奖。离开央美,到清华美院,想法其实很单纯,就是想要建立、发展和完善一个自己认定对的教学体系。在基础教学有效整合之后,再融入我在创作思想上的思考,一点一点渗透其中:夯实基础,大胆实验——要有雄厚的技术基础,还要有观念,有思考,有想法,勇于去尝试。这也是我一以贯之的学院教学理念。
说起来,也是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了,西方当代艺术对中国当时现行的艺术实践和艺术教育体制的冲击,真可谓是摧枯拉朽,简直是一塌糊涂。那时候,我自己也很是迷惘了一段,在心里画着“?”——我们过去的教学还有没有用?我们学的东西还有没有意义了?我着实是困惑了一段,那其实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我一直研究传统,古典,全部放弃,彻底丢弃一切,重新再来,真是觉得太可惜。应该说,我的确也是在北京才得以完成着我对于雕塑学院教学体系上的思考和实践。
3、 798
常有人问我,身在学院,为什么还会进驻798?说到底也还是我的性格使然。如果说当年老师的提醒,北京是一片汪洋大海,那么798于我而言,就是一个职业艺术家的海洋,一个真正的,纯粹的艺术的海洋,是一个英雄不问出处的艺术市场的海洋。2000年开始,我在罗海军借给我的一个工作室里工作。平日里也会在院子里走动,虽然彼此不认识,但就觉得他们做得都不错。2003年非典的时候,就租了现在的零艺术中心,当时还叫零工场,用来做自己的工作室和教一些朋友的孩子学画,按照我自己认为对的方式,而不是应试的方式去教他们。坦白说,那个时候我四十岁了,压力是一定会有的。真正进驻到798,我突然发现自己要重头开始,因为在这里要想获得认可,不是你的学院背景,不是你是谁后面的那个身份和背景,什么教授都没有了,你什么都不是,你只有凭你的作品,你的创作而不是学院教学来获得认可,博得喝彩。
一切都可以归零,从零起步,我会赤手空拳再去搏一次,这也注定了是我自己的人生选择——既在学院内,还在社会中。当然,真正让我感受到选择798是正确的,真正意识到自己到798的价值,这其间是有一个过程的——直至2006年我参加温普林策展的“红旗飘飘飘”的作品《堆云•堆雪》产生和完成的时候,我自己才真正意识到798的重要性。这件作品的产生打破了我以往创作中的一些常规的东西,它是一个延续,也是一种思想的变革,一种自我的颠覆,它和那个展览是同时出现的,说得上是一个合拍。零工场的时候有黄锐策划的《构筑•寓言》,我策划的《临界》,零艺术中心后有温普林的《红旗飘飘飘》, 顾振清的《各玩各的》。我自己最知道,我之所以能创作出《堆云•堆雪》,就因为我在798这里,作品能产生当然是跟798有关系的。在这一点上,我毫不讳言,也深信不疑。尽管,我和798的缘分并不止于艺术作品和艺术展示。
2003年我当选了人大代表, 2004年初,798已经面临拆迁的问题了。在当时人大同组的朝阳区区委书记的支持下,我和黄锐、徐勇、毛栗子、苍鑫、安妮等等艺术家一块儿积极磋商,于2004年2月18日下午,议案提交截至日的当天,递交了以呼吁“保护一个老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一个正在发展的文化区”为题的议案。2005年8月29日,刘琪市长有“看一看,论一论,管一管”的批示。2008年两会召开时,市长来朝阳团听取汇报,我做了有关798的报告,也是在这次会上,他宣布798已经被正式命名为“北京市798文化创意产业区”,进入北京下一个五年规划的报告中。此外,作为人大代表,我还提交了《798包豪斯建筑作为中国近代建筑遗产保护》的议案,以及针对两条市政公路入园,提出《保护一个完整的文化创意产业区》的议案。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会以人大代表这样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参与到798的历史事件中来。我在这些事情中也更真切地意识到了自己身为人大代表的责任意识。在对人大这样一个可以用来说真话的地方倍感珍惜的同时,对政府的信心也会增加。
4、 《堆云•堆雪》
这件作品对我的雕塑创作来说,的确是很重要的一次发声。作品完成只用了四天时间,但是我之所以要做这件作品的理由却更像是我自小的一个心结。那就是一个人的价值究竟应该如何来衡量?一个生命个体究竟应该如何去尊重?
我小的时候,有被人歧视的经历。文革时,因为家庭历史有问题,父亲进了牛棚,自己的家被占了。我住到了姥姥家,姥爷在监狱里,几个姨都去了兵团。那个时候,我没有朋友。周边住着的人后来知道有主马路过道那边的韦尔申,马路这边对面那个院的王广义。那时候是不会有任何来往的。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都属于地富反坏。家里人也会时时地提醒你在外面不要跟别人说话,谁要跟你玩,就离他远一点。那个时候和我最亲的就是身体不太好的舅舅,他吹口琴,弹吉他,打口哨(吹曲)的时候,我就坐在他身边,听着。晚上我和舅舅是两个箱子拼一块儿,对着睡。所以,就是到现在,你给我多窄的一个长条凳,我躺在上面睡都掉不下去。我现在晚上睡觉我翻身我自己都知道。我的这种敏感已经成为身体记忆的本能了。同样地,我对别人看待我的态度也特敏感,因为从小就老要看别人的脸色。我那个时候是小,但是我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那种被别人歧视的滋味。你的背景和你的地位和你自身,别看小,这些东西都懂了。如果把人本身作为元素,再加上符号,也就是背景,就等于价值,这也就决定着你的是与否。回想起来,小时候你经受到这种压力,懂事就特别早。不自觉地,就都记在心里。
《堆云•堆雪》的标题也就是我要说的话。如果你把帽子摘了,衣服脱了,椅子撤了,屏风拿了,也就是把我说的这些都是地位象征的符号都拿掉,她就是一个女人体。就算她有一张慈禧的脸,还有谁会说她是慈禧呢?不可能还会有这样的指认的。所有外在的东西,包括你的名字,如果是一个符号,就都是虚的。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心结,或者说,所有的观众,都会经历这样的问题,都会有切身的体悟。慈禧就是一个符号而已,她之所以会成为我表达的一个载体,是因为她在她所处的那个时代,是起到过重要作用的人,是转折性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当然她也是一个最矛盾的一个人物,对她的解释也是最矛盾的。我的作品就是想要让这样的矛盾和疑问自显——我们究竟是如何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我们究竟是如何来尊重一个生命个体的?
5、 《孔子》
如果说慈禧还是一个可以有具体形象的符号,那么孔子呢?在我看来,哪里会有所谓的标准孔子像?孔子就是一种被历史书写,由文字传承的思想和学说。我的孔子就是这样在历史长河的书写里,一路凌波微步地漂移过来,立在我们的面前,面目不清。他的美髯是披挂的装饰,一双纤纤玉手很漂亮的叠合着。两米高的塑像,上大下小,穿戴的服饰不过是一些处理过的衣纹。满目轻盈里是一种捉摸不透,随时有可能的幻化而去,它强化的是我们为孔子这个符号,多方撷取整合而成的形象的不真实感。或许,任何一个承载孔子的具体形象都会是注定模糊和徒有其表的。我尝试着做一回《皇帝的新装》里那一个口不择言的孩子。
6、 《山丹丹花开红又艳》
有不少的人会把我定义成“红色雕塑家”,事实上,我对历史人物的选择,关注的还是我自身的艺术表达是否正常,是否自然。我要解决的完全是艺术的问题,我并不想去涉及政治的问题。
毛泽东也可以说是我自身主动去熟悉的一个人物,他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人物。和他有关的作品,我创作的有《红星照耀中国》、《我们走在大路上》、《阳光下的毛泽东》、《日出》和《诗人毛泽东》,这些形象也都是有出处的,应该说毛泽东那种骨子里的自信,是一以贯之的,也可以说,不自信就不是毛泽东了。
有了前面很多的铺垫,总觉得会有不满足,很自然得就想到要创作这一件《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我只是觉得,他们是一家人。这是清晨,一个家庭,一前一后的错开站着,还有一只啄米的母鸡,它也是一个生命。当然,鸡是没有立场的。一个丈夫,是诗人,作家,政治家,此时的他有疲劳,有累,很轻松地放下了架子。有人会说溜肩的处理似乎不是那么伟岸。这也是我一直想说的,伟岸的是他的思想,并不是他的躯壳。他的胳膊本身就长,我在这里也有意识地拉长了一点,让他有些下坠,放下的感觉。他是扎根农村的泥腿子,长衫长裤的,夹着烟。此时的她,作为妻子,还是一个从大上海来的志愿者,一个志在颠覆自己生存环境的青年,活泼泼地站在这里,束着腰,裤腿挽在膝盖处,整个人的状态是怀揣热情,乐观向上,笑着的模样。这里的形象是我的艺术创作,但也都是有图像资料的出处的。艺术化地处理和表达,我只是不愿意刻意地去回避一个在塑造毛泽东这个作为普通人的非凡者时,必须要直面的一个问题——他的家庭——这是我尝试作出的一个努力,尊重每一个体作为生命存在的权利。不同的人来看总会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我也还是希望都能站在艺术的角度,人性相通的立场来回看我们对于历史的解读。
很多人都会去做毛泽东,真的难做,因为看的人太多了。他的神态和状态,应该如何去拿捏,挑战很大。有的人想表现毛泽东的轻松,但轻松不起来,有的人还在文革的思路上,于是,绝大部分作品都会以纠结而告终。事实上,如果能把毛泽东当普通人来做,你就不纠结了,但很多人把握不好这个普通人的尺度,还是因为对毛泽东这个人不够熟悉,揣摩得不够。我做的毛泽东,曾经让一些个人很感动,还有的人说流眼泪了,原因是他感觉我创作的这一个毛泽东把他拉回到了那个毛泽东还不是伟人的时代。我想要通过我的雕塑作品传达一种情感,由内而外的,一种人性的穿透力量。作品是可以和人心相通,和人交流的。
7、 《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
这是1998年受舒乙先生的邀请,我为巴金塑的像。现在看起来,我想要通过自己的作品传达的情感和对于人的存在最本真的尊重一直都很自觉,很强烈。正如作品名字的意思,首先是一个小老头,然后才是巴金这个符号。因为要塑这尊像,在得到巴金先生的同意后,我在他的公寓里住了两天。我给他翻了手摸,推着轮椅上的他在西子湖畔遛弯。这说得上是最近距离的一个接触了。吴冠中先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慨:当我看到李象群的这尊巴金像的时候,虽然只是一个很朴素的,很普通的小老头,但能感觉小老头背后是一种伟大的力量。的确,我自己也习惯了这样一种端详,背着手,低着头,往前走,脚稍稍往里扣着,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小老头,却是一个内心如此强大并且传递出力量的老人。
8、 莫唯•女孩•小女孩
《莫唯像》是妻子给学生做模特时,我为的要做一个示范,很轻松地就一气呵成了。快二十年前,也做过一个《莫唯像》,因为妻子突然剪了短发,就放下了,没做完。不曾想这一示范,还了了妻子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作为肖像,作品获奖了,理由有三个,一个是技术层面的,国际一流水平;一个是体现了东方人的基本特征和状态;还有一个则是白铜材料的使用,这个年度展连续几十年了,第一次出现白铜材料的肖像作品。我之所以选择白铜,是因为它的特性如同白银,看似朴素、一般却暗藏着一种贵气和雅致,和银一样内敛却比银要坚实和多一些光泽的变化。
《Burberry女孩》也是上课的时候,给学生做示范,现场完成的。模特很漂亮,肤色偏深,先是示范做的人体。然后后加的衣纹处理,这件风衣是浅色的。人和衣服相得益彰,的确是蛮单纯的,有一种动人的美。
《午睡的小女孩》则是朋友的小孩子,一直希望我可以给她做,为孩子留下一份童年的礼物,或者说记忆,证据, 又可以说都有。碰巧那天,大人聊天的时候,小孩子玩累了,趴在沙发上睡着了,安静踏实的模样,真是无忧无虑,酣然入睡,甜甜地作着她自己的梦。我也是一蹴而就地完成了这件给她的礼物。当时真是有一种舍不得唤醒她的感觉。
这一类作品,都是随意即兴而做的,出来的效果很好。大家都觉得很灵动,意味也好,技术没得说。对其他人,可能要花费很大,甚至全部的精力,也不一定达得到,对我来讲,的确是最容易的,这其中的分寸把我是我随手就可以拿捏的,自然也会带有我对于对象、材料和形式等等因素基于理解上的,完全出于本能的把控和真情流露。
9、 紫禁城
紫禁城是我正在完成的一个作品,虽然作品的题目没有完全确定。我个人感觉它更像是针对一个建筑空间的造像行为。当然,这里有一个超出建筑物理空间的更大的一个空间,实际上是在为一个文化空间造像。整组作品的布局很大,铺陈开来会有200多平米。作品是一个整体,切开25块,唯独太和殿没有从中间剖开,是一个完整的,在它的前面有一个人在奔跑。其他的殿,有的从中间剖开了,有的分离了,瓦盖拿掉了,有梁,有内部空间。我是在运用雕塑的手法,写实的,来完成它的肖像。它也是一个生命体,有的是弯弯曲曲,不完全是横平竖直。地平面是用白铜铸造的,非常平,如同镜面一般,上面是刻度坐标,很精致。 一对比,雕塑本身,就很颓败。基座是布满展厅的不锈钢管做的脚手架。不锈钢和白铜,灰和白,色泽会特别漂亮。让人看了,会觉得不知道究竟是在建呢?还是在拆?那个奔跑的人,也不知道是在进呢?还在在出?
我第一次去故宫,是大三的时候,母亲在北京医院学习,她说你过来看一下。我12月份来的北京。以前感觉神秘得不得了的东西,突然置身其中,就在眼前,就觉得人太渺小了。那一种横向的延展,让你有往地下趴的感觉。它和后来去的欧洲的教堂完全不一样的心理体验。教堂是让你往上升,它却是要把你压下去。你就感觉之前看的图像太没有感觉了。它远比我想象得更有压力。
可以说,紫禁城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它是一个具象的,物质的文化,也是一个传承,它要说的话,要说的东西太多。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我一下还说不出来,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把我的表达做出来了,就在我的作品里。我希望能看到的人,在忘言的时候,心会动。
10、如何传承和如何当代
在我看来,传统和当代不是一个能截然分开的东西。我感觉自己一直是一个脚踏两只船,两条腿走路的人,所以对于传统,我理解的就是技术的传承,对于当代,我理解的就是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是有的放矢的表达。
我们过去不太关注传统。以我自己为例,是从革命现实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再从现实主义转向技术这一块的。技术其实就是本体语言的认识和探索。中国技术层面这一块其实是太不够了。或者说比较落后,技术层面很低,还是初级阶段,手段很少。技术层面这一块,也就是雕塑的本体语言,我一直在研究,三十年了,一直很投入地在研究。希腊雕塑、埃及雕塑,和中国古代雕塑,我摸了个透。在我看来学院本身就是一种传承,没有传承就不成为学院。学院必须有技术上的传承这一块,也就是雕塑本体语言这一块儿。
当然,我还是会特别关注当下。可以说没有社会的责任,我就不能算是艺术家。我的存在也就没有意义了。吃饱喝足之后的怡情怡性对我来讲不重要。人要做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要做一些重要的思考和表达。你要传递给观众一些信息,能让他们在这个信息里获得什么,能够再去做一些什么,这特别重要。艺术应该提出一些问题。人吃五谷,没有不生病的生,社会也一样,我们的艺术也要能够给社会的疾病作一些艺术的诊断和艺术的治疗。我认为这是艺术家的责任。技术的传承说到底还是更好地为表达服务的,当代则是艺术表达切入社会的立足点。
研究生阶段,我学的是中国古典雕塑,中国古代传统雕塑。我做的雕塑还是西方传统雕塑体系里的东西。有些人会觉得奇怪,认为不搭界,我个人觉得其实一点都不冲突。它们之间都有共性的东西,根都是一样的。可以这么说,通过东方我解开了西方。具体而言,就是我通过临摹东方雕塑,我把西方的雕塑语言给解释通了。同样地,我又通过西方雕塑把东方佛像的造型,尤其是对于形体的认识和理解,我也给它弄明白了。我临摹汉代雕塑,常有不可思议之感。就在于它对形体理解的深刻,甚至比希腊雕塑还要精辟。
希腊雕塑,它是充分运用了几何体的概念。几何体是一种观看方式。你视对象为不规则的几何体。用几何体的眼睛来看待一切,就能把非常繁乱复杂的东西先简单化。然后再来不断充实这个几何体,让几何体特别简单的一个形态里,内容会更加丰富。一经选择,提炼,它会让你看到的东西比繁乱本身更多。应该说,雕塑本身更像一个战略而不是战役,小的战役只能是一些噱头,一些动人的局部而已。
汉代雕塑它也是从几何体来认识一切的。它的点线面,在形式认识上的深刻层度 那又是比希腊雕塑要更高一层 。不得了的认识,只不过没人说而已。 过去说东方不了解解剖,没有这个认识。其实不是这样的,真不是。它的认识太深刻了,它都装在里面去了,全在里面。你拿一个雕塑作品来,每一个小结我都能给你指出来。真的是特别精辟的认识和处理方式。我没有理论分析,我完全是靠我的手在做来理解,来分析的。陕西、山西、银川、四川,汉,唐,宋的作品,我都有临过。在这期间我还碰触过玛雅文化和希腊古风时期的雕塑。东西方的比较,它们之间都有联系,它们肯定是通的。如此一来,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去做了。
应该说,从塑像出发,我总结了两点。对我后来教学起重大作用的两点。应该说学院适用的,也是基础教学必须传承的——第一是科学的观察方法。观察方法,先走纵向,再走横向。只有这样,才会一点都不差,很准。文化也有纵向横向,历史和共时的观察。第二是要认识到任何物象它都有规律。这规律实际上在数学里就是公式。它可以有数值的变化,但规律不变。形态在变化,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规律不变。
举个例子,比如谈结构。一路受教育以来,很多老师都讲,但他们讲的结构就是解剖结构。我认识到的结构不完全是这样。它是诸多的结构——第一空间有结构,第二形体有结构,第三才是解剖结构。此外,从社会学来讲,社会有它的结构。我就是这样来解读结构的。在教学中需要拓展大家对于结构的认识。再比如关于写实和具象,两者要拉开。写实和具象是两回事。是两个概念。写实其实就是写生。创作是思想,把你的想法和理念放进你的作品里, 用你的手段来创作的作品,这里面不存在写实。它是一个具象了。写实这个手段必须要有。但写实只是办法之一。观念是想法,有想法没办法不行。这样大家把这些问题认识得更清楚,更透彻。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要流汗,头脑之中要流汗 头脑之外也要流汗,要动手。我始终认为技术是基础,是根本。我可以说,和雕塑有关的每一个技术环节我都了解,都清楚,都亲自上手做过。我对每一个程序存在的可能性和潜力也都心知肚明,算得上是门清。在如何传承和如何当代之间,我的雕塑理想就是想要还原人,还原社会中形形色色的这一个人。很多雕塑家在技术,在雕塑本体语言上都给过我启发和支持,比如米开朗基罗的肌肉,罗丹的文学性,一种抒发和贾科梅蒂的符号化等等。但是我总觉得他们都没有真正还原人。他们都是给了这些人一个角色,来成全他们自己,而在人性的表达上,我觉得都不够好。西格尔的真人, 在我看来那是物,在情感上没有互动。
我相信我只有技术层面很雄厚了,有手段,有方法,再有当代人的思想,我就能做得更好。或许,我不会一下子做到更好。但是我每一步都在往那个方向推进。我一直都在思考,思考一些问题。有时候,别人来看我,我似乎只抓到了一个点。但它可能有一个更大的现实层面,那它就不是单纯的一个点了。甚至是我自己可能意识不到的,但别人可能能在我的努力中发现脉络,也看到价值。
访谈后记:
固然中间——是我在和雕塑家李象群访谈之前对他和他的雕塑的一个印象,也打算作为一个拟定的文题。只不过,当我把整理的访谈文字,再通读一次的时候,如此明晰的李象群跃然话里字间,我再有什么说辞,都显得有些多余,矫情和不合时宜了。只不过,有那么几句感触,还是想说出来的,是以为记。
艺术于我,我始终是个学生,边学边看,难免会有些自以为是的揣测之处。五年前,有机缘介入展望《新素园石谱》的文字编辑工作。于是,便妄下断语地认为,当代雕塑的最有价值之处,应该还是会落在新材料,新的工作方式和定义雕塑的新概念这三个选项上。如此三选一的条条框框之下,幸存者可谓寥寥。难道,这也是李象群缺席当代艺术批评视野的原因之一?
知道李象群,是因为那些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的领袖像和名人像,不明所以地竟然会在这些定义为“红色雕塑”的作品中见到如此纯熟的雕塑语言,如此灵动的细节,如此微妙的手感和如此传情达意的泥料的拿捏。人们叹服于雕塑家的天赋和才气,称赞其作品中雕塑语言的纯正和精湛的时候,却对其作品中可能的人文关怀和艺术指涉语焉不详。难道,所谓的政治正确就一定意味着艺术性的缺失吗?
我们在检讨相关美术史写作的时候,会意识到在二元论价值判断下被牺牲掉的那些中间状态,如何能够再次进入和充实我们的知识架构,是值得庆幸和期待的挖掘和发现。那么,反思中国当代的艺术书写里有关现代性阐述的缺失,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看到尽管有关艺术本体语言的深究,在西方艺术体系中当属现代艺术的范畴,但是它对于当代艺术中的矫枉过正,却是不无裨益的。李象群的雕塑理念和雕塑实践自有其历史的逻辑和现实的取舍,于是,这种固然中间的状态,又将会以何种面目成为我们未来美术史写作的材料呢?只是拭目以待,显然是不能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