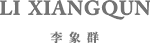一
黑与白,截然相反的两种颜色。没有比这两种颜色显示如此鲜明的对立性了。正因为如此,它们走在一起,成为不可分离的一对,如阴阳,如男女,如昼夜。
黑与白色的精神象征——正如自然界通过时间的每一波过渡那样,投射到人们的视网虹膜,产生X色光的折射及其它反响,首先成为思维跃动的平台。继而,因为它是双性的,它被输送到反应性激素的神经中枢里。
黑色无光,或说无色,成为背后的,地下的,梦的世界。在另一种情况,黑色也是暴力,对暴力的接纳:黑暗,黑手,黑社会,黑户口,黑工或黑商。黑色成为反面的渠道,因此如同人间对黑色现象的认定一样,黑色可能是最流畅的颜色。它是黑的,它即高贵。它是黑的,它即悲怆。它是黑的,因此将征服对方并且有无法预料的力量。
白色也是颜色并失去颜色。也是光却没有光源。一梦初醒的印象是白色的。童贞女的美丽没有限界,因为她属于白色。新嫁娘将拥有最美丽的瞬间,因为她放心大胆地用白色装扮。反过来说,愚昧无知也是白色现象,信息封锁与言论专制也应该是白色的。自由的丧失与争取自由同样以白色隐喻,因为漫天的白雪覆盖了日常的阴暗。白色的烟雾产生美丽的幻觉,然而它含有有毒物质。
我们无法辨别黑与白,因为它们已经清晰存在,成为事物的两面。我们无法清楚两面性事物的真正定义,转换,混淆,差别,这些需要费神解释的字眼充满悖论,更不要说“颠倒黑白”。
在西方,生命的降临象征白色,死亡象征黑色。在中国的大部分地方,死亡同时是白色——葬礼的服饰掩以大片白色,死亡成为阴界里的再生。
在视界世界,黑与白获得了永恒的声誉。黑与白的视觉力量强大到代表历史。上世纪前半的艺术史天才辈出,也充满黑白两色时而泾渭分明、时而模糊的幻象。本雅明是的,卓别林也是的。彩色大师毕加索最伟大的作品“格尔尼卡”是黑白两色的。
黑白两色永恒地印证了易经里阴阳两者关系的永恒性。
二
顾名思义,这是一次唯有黑白两色作品存在的展览会。
除去作品所呈现的颜色特征之外,它们还具有表象之下的特征——色彩与表象的合作,冲突和分裂。最光鲜的白色作品——杜尚的小便池一直处在用途与作用的概念分裂之中。除去颜色所代表的立场之外,颜色与物品在艺术里产生的交错——其动作及差距都是必要的条件。我们喜欢白色的平滑,因为它嘲弄了日常与客观现象。我们接受黑色的高雅,因为它是一种反规则。我希望参展作品具有某种侵犯性,某种犯罪感,反之不构成对世俗意识的质疑,或否定。
相对性经过艺术的升华成为否定性。它们有艺术魅力,有人性魅力,有性魅力。相对色相产生出的艺术否定同时是历史的、社会的、哲学的、政治学的魅力。
所有黑白颜色里的意义不可能概括在这个小空间的展览会里,毕竟它缺乏历史的机遇与天才作品。但意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即颜色是政治的,它在艺术里的最终表达是非政治的的观念。因此这个展览会也将会是非同凡响的,它既提出口号,也敢于竞争。
反过来说,没有社会隐喻的黑白色作品将是单调的,没有性隐喻的艺术作品将是庸俗的,如同那些司空见惯的粉饰主流消费商品一样。这个展览着重提示一种重叠感觉——艺术与非艺术因素的重叠。激发,引起感官的惊奇——而这种效果只针对灵魂的运动者,除去精神健忘症者。
黑、白色艺术作品的穿透将反映现实世界的昏暗及吊诡,这成为展览概念的本质。除此之外,对主题、材料、形式、内容、表现手法等均无限制。
三
“我们仍有希望,在能看到的时候”,邵译农跟我说道。我想到顾城的诗句:“我有一双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寻找光明”。
最近慕辰和邵译农迷恋黑色,他们给许多装饰物品上绷上黑羊绒——可可·香奈儿说:“黑色包容了一切。”他们给一切包容黑色。尽管他们的工作即是掩饰,这种在技巧与材料上的拘泥似乎在掩饰另外的什么。或许,面对既定的装饰全部是伪造的现实,必须再度加以伪造,以便换取另一种真实:被包容,被消失,被象征及极度异化的真实。
隋建国一向以具有视觉意义的文本作为素材,如“中山装”,如“中国恐龙”。以隋建国的作品举例即可包括中国当代艺术的处境及含义。历史与当代,文本与视觉符号,归根结底,是意识形态的描述与背离。或者说,一种典型的政治题材与艺术形式纠结的错误引导与发现了其中的创造。它是被加工出来或作为实验的样本“创造”出来的。正如隋建国这次的作品《折叠空间》一样,他提供真实,同样奉上虚幻的空白,两者成为互补的作品状态,在观看与想象的过程中弥合,使观者同时怀疑或是相信作品竟是真实的。
李象群的雕塑堪比实物——与作品相对即无法忽视对象。所以我们无法忽视他创作的毛泽东,慈禧,及这次展出的梁思成。李象群以迅疾的手法再造“虚拟”——既往人物的写实雕像,这种写实的真诚与恍若隔世的浪漫情调赋予人物一种材料性的温暖,尽管具有学院主义的真实形态,李将“人物”置放于“虚拟”时间及空间的技术塑造上,这些不可思议的真实人物出现在空间里,仿如纪念碑,亦仿如擦肩而过的普通人。严苛的历史记忆就此消失,这是李象群一人独在的驾轻就熟的伎俩。
我经常对张大力的作品感到共鸣,他是一名行动分子,创造了涂鸦大头像与AK-47的符号。但同时他是一位思想敏捷的人,创造出,更确切是发现了新闻摄影中的《第二历史》。如此说来,他的作品关注两个主题:生与死。涂鸦大头像,可以说是生之记忆,生之叫嚣,AK-47则是死亡,一种宣告生命终结的近当代符号。这次,两个主题的对立视觉放大到他的巨幅画面上,让我们清醒我们的存在。
郭工的《一棵树》非常直白,直白地可以看见刨削出的木纸上隐约显现的文字:自然如此纤细,如此洁白。而现实则仿佛手臂一般伸展的树枝,发出扭曲的无奈的暗哑的叫喊。这就是围绕着我们的环境——经济发展,技术发达,自然资源毁坏。一无所顾与戚戚哀婉,隐私与暴露都缠绕并展开其中。
与郭工的做法相反,苍鑫的《精神颗粒系列》是先把原木剖成所需形状,再将其烧成黑碳状。其立意,即艺术家一再讲述的金、木、水、火、土的五大物质元素的关联性,仪式,生命时间的循环过程。毋庸置疑,苍鑫的作品一直具有某种异教的神秘感和原始人类的悲壮气息,这原本也是艺术家刻意追求的。如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古代人比现在的人好,他们与神明更接近”。我以为这些作品即符合了艺术家的个性,又在复杂立意与单纯表现的矛盾中得到净化,是回归于本质的佳作。
水泥是一种奇特的材料,一般是较为难看的,有时却会出乎意料的出彩。比如说在这里展出的刘建华作品 《圣经》,亦是以水泥材料的成功试验。
不同于别样物质,中国艺术中的陶瓷作品总是做出归属性答案。这些年来刘建华的陶瓷作品总是得到关注,从他的旗袍系列开始,作品常在一个背景下被赋予名称或某种价值。以致艺术家一直在摆脱陶瓷艺术家的光环,重新开始。总有一些东西可以塑造成形,不仅仅是记录下来,加以证明的对象,因为是刘建华,一种难以名状的自传统一路走来的造物之手。
过去刘勃麟曾经使自己隐身于各种人为制造出的背景——商店,公路,涂着标语的墙壁。这是一系列的制作过程:先请人模仿背景将自己画成背景的一部分,再拍成照片而展出照片——照片是一部被人工社会量化的背景,隐约可见艺术家的眼睛。而这次的作品又返回(早期作品)人体的立体形态,每个人体的肌肤表面嵌满了手机的充电器,所有人体笼罩在黑色的线网之下,朝着同一个方向爬行。这反映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人体从属于信息制造的系统,依凭机械的动力与规则统一行动。本雅明所言“时至今日,谁总是取胜,谁就行进在凯旋的行列中。”。
蔡志松曾以铜、铅材料制作过一些类似兵马俑的人物雕塑,这些人物赋有造型张力——即来自古典,又来自学院式的写实技巧。我看这些作品总有种莫名其妙的传统气息,好像出自古代人之手。当然不是,除了佛教中的造像艺术,中国自秦汉以来的人物雕塑史是被断绝的。对于蔡志松的新作品,我看到一些网上流传的微词。我倒觉得变化出于表现手段的自然,或处于一种创造力流动的自信。其实,对成功与即定方式的放弃是一种很大的自信力,只有好的艺术家具有这种自信。
这一章的终结我愿意叙述展望的《药片佛》——尽管佛像是一种概念的塑造,意味了此类艺术品的幻想空间与创作过程。佛为宗教,药为科学,《药片佛》因两者而成艺术。相信我们依旧对自己提出问题,并回答方案。如果依旧抱有对神明的虔诚的话,药与佛的实验不愧是一帖自我迷幻的解咒之符。




观众在欣赏李象群的作品《印象·China》

李象群与策展人黄锐(右一)在展览现场交流

李象群与参展艺术家蔡志松在现场交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