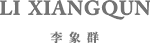采访人:马文甲(以下简称马)
受访艺术家:李象群(以下简称李)
 马:
马:
李:现在雕塑的概念已经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雕塑。我的理解是雕塑就是形体占据的空间,立体性的实在物象都可以被称为雕塑。所以装置是雕塑,行为艺术也是雕塑。雕塑成为了一个大概念,但前题是作品创作的视角和表现是艺术的。也就是说,一切在一种意图性的创造下而产生的具有实体性的立体的作品都是在雕塑的范畴之内的。
马:雕塑概念既然如此,那么具象雕塑的界定是什么,它的概念或者说内涵有多大?您为什么会选择具象雕塑?
李:很多人认为具象雕塑就是写实,这种理解其实并不准确。具象雕塑是个大的概念,写实是具象雕塑中的一个门类。写实是对客观存在的对象尽力模拟和描述。作为具象是作品的刻画结果与描摹对象之间存在外观上的逻辑关联,或是要素对应。当代具象雕塑的概念也和传统概念不同,它可以横向展开。其实具象可以理解成为具有具体形象的意思,那么什么才是具体形象则是一个接踵而来的问题。以前我们所说的形象多指人或者是具有体貌和五官的生命体,像动物和昆虫等。而现在经由现代主义艺术的形式探讨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单纯的形状和色彩也是具有形象的。形象可以理解成为一种外观与一种特定的指代信息的关系。如同中国画中的松、石、水都有着自己的独特形态,他们都能使人们联想到一种精神,那么他们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就具有形象性。这样一来形象就不单单是细节的概念了,而是一种可以逐渐推演的概念。而我选择的是具象雕塑中带有写实因素的一种,仍然是在造型性和特征的秉持中来进行创作的。我的具象雕塑创作近期都是肖像,因我在研究中发现其实肖像还是雕塑创作中最难的,因为它的难度和水准是有着较清晰的参照的。并且肖像也可以具备很强的观念性,只不过这种观念容易被技艺性所遮掩,但在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的观看者那里对于任何观念的解读都是无障碍的。
马:就像您所说的如果具象雕塑的范畴也是无限大,那么在雕塑领域内其他状况的雕塑艺术的生存空间在那里。
李:其实一经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好多的概念越往深里研究所展开的面就越大,没有一个概念是有限的,一成不变的。就像你一直在问我关于概念的所含和边界,我是做实践的,我对概念的认识当然是在随我的实践向前而推移的。如果你问的是做理论的学者,那么他们可能出于收编和比对研究的需要会对某个概念有比较清晰的界定。其实,如果站在区分的角度来看,雕塑领域中具象雕塑并不是占有所有的份额,只不过在时间的脉络上看具象艺术的延续性最强,数量上可能也占大多数,但站在概念的角度上看他只是雕塑中的一个分支。我没法说别的雕塑形式有多少生存环境或是现在状况怎么样,毕竟我的研究没有聚焦在那里。但我可以告诉你具象雕塑是靠形象的直接逻辑来表现观念的艺术形式,每个起伏和形体都是传达信息的要素,而不仅仅是观念的传导因素。
马:您对具象雕塑进行研究的途径是怎样的?或者说哪些雕塑的研究对您的雕塑观的确立和现在的艺术风格的形成影响最大?
李:我的研究是按照传统雕塑训练的脉络走的,同时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和政策的影响。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大学期间完全接受的传统教育,受俄罗斯革命现实主义的影响比较大。那一时期许多革命现实主义的雕塑是我们全国美院雕塑系的学习教材,我们在努力的研究解剖和惟妙惟肖的临摹对象。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文化艺术得到了全面的介绍,我在这一阶段看到埃及、希腊、罗马、米开朗琪罗、罗丹等等的雕塑作品。之后大概用了三到五年时间,对这些经典进行深入地研究,当时在技术层面上有一定影响力和实力。因为对于同时进入的信息说最具诱惑力的当然是最新的事物,所以我最先研究的是罗丹和布德尔。这你在我的本科毕业创作和研究生的习作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他们的影响。而后来我对希腊雕塑和埃及雕塑的研究是我看到了概括表现形式的魅力和传达精神的力度。这一阶段主要是我认识到艺术表现而非表达的重要性。我觉得表现性才是艺术的核心。改革开放使得西方艺术从80年代末开始对我国艺术产生影响,在这期间,中国艺术市场受到西方文化、经济的严重冲击,传统的艺术教育几乎土崩瓦解。我国的当代艺术就是发起在这一时期,当时“实验”是艺术的总体标签。我在这段时间内也创作了大量的材料性很强和观念性很强的作品如《融》等。90年代末到2000年初,中国的艺术教育开始逐步调整,并且产生革命性的转变。这是我则专注于肖像的研究和创作,我竭力忘记所有记忆中的大师和艺术准则,开始开拓属于我的艺术空间。
马:在教学方面,您主所强调的基本功的概念是什么?您注重培养学生哪些方面的能力?
李: “夯实基础,大胆实验”就是我提出的学院教学的方法。我们进行的形态研究不仅是为了写生、写实、简单地塑造一个人,这种对形态、形体的了解是为了创造出未来更多未知的物象,这也是我们的教学目标。对于造型艺术来说,研究造型、形态十分重要。形态研究一直是美术学院研究的课题,并一代代传承下来。学院需要传承,但考虑到雕塑学科的发展,在教育当中还应当体现大胆实验,实验会产生未知的东西。我还提出一种“综合教学办法”,即要求学生必须对空间结构、形体结构以及解剖结构都有充分的认识,这三个结构不仅仅针对人,还针对所有物象。比如工业设计、建筑就都包括这三个结构。而在创作中要应用所训练的空间素质和对材料空间的把握来进行具有社会意义和思想性的表达。而不是仅仅用所学习的人体知识来应付社会和生活带来的提问。
马:您如何看待雕塑造型和绘画造型之间的关系?有人说学雕塑要放弃绘画的思维,您认为怎样?
李:它们之间是平面和立体的区别。绘画运用的是平面思维,它对影像有着特别的关注;而雕塑运用的是空间思维,它是占有空间的。雕塑的关注点在于其自身对空间的影响,以及空间对它的影响,这是一种相互作用。而当空间研究建立起框架时,绘画的造型和观察方法会给与立体艺术以给养。准确的说为什么用绘画来充当所有艺术学科的入门课程,这是有原因的。因为绘画材料比较容易进入反而能使学生深入视觉规律和艺术表现的研究。这些虚实、疏密等绘画要求其实正是视觉语言的要领。当在雕塑中建立起立体框架之后,要靠黑白灰的色界关系来区分转折和形的包含关系,以此作为深入处理性题的出发点。所以雕塑在进入后期处理和深入时所经营得准则是绘画型的,更是视觉语言方面的整合。所以不懂绘画或不重视绘画功底终将会影响雕塑的发展。
马:您认为具象写实雕塑这种传统的手段该如何在新的社会生活条件下迸发活力并介入当下?
李:具象艺术的手段是塑造形象,这种形象是最容易进行解读和能够带领进入思考的最直接途径。这一点是的具象艺术在什么时候都不会消失。尤其是在这个到处都渗透着效率意识的时代,具象艺术更是会受到更多关注的。而在更加重要的层面上是艺术家所要表达的内容和信息一定是要具有当代意义的事物。当下艺术家首先应该明确自己所处的位置,明确自己应该思考的问题,及应该担当的责任。我在自己的创作以及教学过程中都提出,首先要对社会进行调研、思考,在现实中寻找自己最关注的问题,然后完全以自己的思考方式解读这些问题。但这种解读不能站在判官的立场上,艺术家没有权力判定对与错,并且很多东西本身就是辨证的。所以说,把问题提出来比什么都重要,当然你提出的问题是不是当下社会所关注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把问题提出后,让大家去关注它,去判断是正确还是错误,是可以解决的还是不可以解决的。这里边思考的成分更多,不会直接给出答案。
马:当代艺术更多的是提出问题,您觉得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么?
李:关于这些问题,不同的艺术家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很难说哪一种更好。并且有些时候,提出的问题会与解读方式产生矛盾。比如有些艺术家以环保为主题创作作品,似乎特别关注我们所生存的环境,但他所利用的材料都是破坏环境的,这就产生了冲突。
艺术家更多时候是在提出问题,当他有能力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要去行动,并且这种行动应该在现实中让大家看到。一直以来艺术家在社会层面的价值体现远远不如政治家、经济学家、军事家,他们可以推动历史的转变。我长期思考艺术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艺术家应该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如何对社会产生影响,从而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2000年左右,我对于这一问题特别的困惑甚至苦恼。所以我在两个方面进行一书对于社会的干与。一个当然是创作,更准确地说是大型的公共雕塑,首先要重新的认识和思考历史,并且将工程当作创作来做。这首先就是匡正雕塑创作的草率之风。而是从雕塑教育方面,年轻一代是未来的主力军,对于他们的教育本身就是对于未来社会的干预和建设。我多年来铺在教学上的时间远远多过创作。我开办0艺术馆的初衷也是给学生一个在社会上检验自己的平台。早早的认识到创作的重要。
马:您觉得798雕塑的生存现状是怎样的?
李:由于艺术市场受到经济的冲击,798的艺术家工作室逐步淡出,新进入798艺术区的大部分属于文化机构。同时商业性的经营机构明显增多,如咖啡馆和创意店。参观者的成分和心态都有所变化,之前来者的有文化名流和艺术学者,他们是来研究和体验艺术的。现在多是些年轻人和旅游群体他们是来拍照、度假的。雕塑展览虽然不多,却仍然存在,但是在我看来,除了0艺术馆可以作为一个相对学术化的平台,其他的雕塑大多数是水平不高的展示,前沿艺术越来越少,雕塑的实验也越来越少。这是十分让人担忧的。
马:零艺术馆定位是画廊还是美术馆?您创立这个艺术机构的主旨是什么呢?
李:最初因为没有定位,叫做零工场艺术中心,现在我提出叫做零艺术馆。我想强调一点,艺术馆要有自己的定位,它是一个学术交流展示的平台。零艺术馆的发展方向不是画廊,它里面有很大的学术比重。我想把它作为学院和社会交流的窗口,让学院艺术了解社会,看到市场;也让社会更多的了解现在中国的学院艺术和教学。艺术馆里展出的大部分是实验性的艺术作品,将推出实验艺术的新人。学院教学体系出来的学生有雄厚的学院基础做根基,如果他们能把自己对于社会的理解和生存态度释放出来,提出观点,那么这些作品是十分值得期待的。
马:您年内的创作计划和展览计划都是什么?
李:我计划在11月份做一个新作品发布展。我在这些作品的创作中抛开了各种束缚,更多地去体现人性的东西。我更喜欢人类之间的平等关系,不太愿意把符号过度地呈现给观众。经过思考我总结出来一个公式,即“元素+符号=价值”。元素是人体本身,是生命的本体;符号是在文化的长期积累中产生的标志性元素,人物的身份就属于符号。在我的作品《巴金》中,小老头的形象是元素,“巴金”是符号,“巴金”使作品的价值发生改变。《堆云堆雪》也是这样,如果把各种符号摘掉,她仅仅是一个女人体。加上身份符号,就改变了她的价值。这也是我过去和当下都在思考的问题。
马:您做了大量的名人肖像雕塑作品,您在创作之初切入创作的切入点与之前的别人对于该人物的表现有何不同?您的具体思考是什么?
李:我一直在想如何让别人在我的作品中看到一个可信的人、一个普通的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去掉他的背景、符号。创作伟人像、名人像我首先想到的是他真正自我的东西,那就是人性的本体。我将他还原成普通人的原初状态,这样观众就和作品就拉近了关系,才能在其中体现这个人的真实。另外在雕塑的处理上我并不绝对的强调雕塑感,将硬梆梆的体块作为基本的表现要素。我更加的强调造型性和视觉规律的研究,所以你会看到我的雕塑与之前许多的大型雕塑在手段和认识内外两个角度都存在着极大的不同。
马:您想让我们在您的作品中感受到一个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人,是么?
李:是的。就是想在观众不知道人物身份的同时也感受到他的亲切、真实、可信。这种塑造才是深入骨髓的。我曾经专门去过延安几次,坐在毛泽东办公桌前慢慢寻找他的感觉,有那么一刻突然觉得自己就是他,感觉特别地理解他。通过这种情感的互动和对话,才能把他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活的人。想要做到可信,就得把这种“感同身受”做出来。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去尊重每一个生命体。我们的作品不仅要当代人觉得可信,也要五百年后的人同样觉得可信。
马:您是如何看待中国雕塑的现状?
李:中国当代雕塑不如绘画、实验艺术等发展得快。这跟雕塑需要占有大量空间及较多的经济支持有关。现在雕塑分化为社会艺术家群体和学院艺术家群体两极。体制内的即学院艺术家群体更大。也是因为雕塑对空间和经济的较高要求。社会艺术家群体非常小,大多以商业为目标做雕塑,对社会的关注还不够,对社会问题的探讨也流于表面,他们毕竟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雕塑要像绘画一样发展不太可能,其自身创作条件不像绘画一样便利、轻松。首先雕塑需要驾驭的元素较多和体能消耗较大这使得雕塑的学习时间较长,有五年制,单个作品的完成周期也较长,而艺术家的创作生涯会较短。年龄大了以后眼睛和精力都不太适合雕塑的再创作。所以做一个好的雕塑家是并不容易的,尤其雕塑在社会工程方面也有着较大的承担。在业务队伍上也有“架上架下”的分野,同时又将从事“装置艺术”的雕塑家从雕塑队伍中分出去作为“当代艺术家”。种种现象时的雕塑创作队伍在技术和观念两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落差需要弥补。
马:您是如何看待塑痕性的雕塑作品的?您在雕塑创作中是如何利用塑痕的呢?
李:塑痕,尤其泥塑的塑痕,是艺术家无意间的流露,并不是刻意表现的。我的雕塑塑痕可能比较多,但都是无意表现的。我觉得这和绘画的笔触是一个道理,都是习惯性的东西,都取决于你如何表达自己。我自己都意识不到是怎么做出来的。但是要能够在塑痕出现的时候判断出哪些是有用的那些需要再做或是抹掉。这是在长期的深入的研究中所锻炼出来的言的能力,但没有详尽的法则可依。
马:西方雕塑语言与中国传统语言从造型的层面来说有何区别?为什么会这样?
李:我觉得中西方雕塑语言是由于文化不同所产生的追求和认识上的区别。它们所表现的东西还是有相通之处的,也都以体现物体占有空间为目的。只不过受到不同文化传统和地域影响,产生了不同形态的表达方式。举例来说,秦汉艺术和希腊化的艺术,巴洛克和中国清代的艺术都有着相通之处,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会自然地从作品中流露。而西方的学术研究传统就是自然科学的,想尽办法去征服自然,解释现象。基本上对于艺术也是一样,是在科学的解剖结构和比例视角等诸多科学角度来定位的。而中国就截然不同,古人的着力点都在人的本身。需要自己对自己有一种办法。窥心、养神、忍、悟等等都是需要一名想来达到一种清明自觉的效果。艺术也是一样总是“得意忘形”,东方的认识和文化发展是更加人文化的,在准意义方面是更加艺术化的。
马:如果说过去您认为米开朗琪罗和罗丹是两座大山的话,对您而言现在还是这样吗?
李:是的。米开朗琪罗、罗丹,还有亨利·摩尔、贾科梅蒂所处的时代都是雕塑史、艺术史的转折点,他们作为一个历史阶段艺术顶峰的地位永远无法取代。即使当代人认为他们过时了,但他们对一个时期雕塑艺术的引领作用是任谁也诋毁不了的。他们为后世的雕塑创作开启了广阔的空间,至今仍然在被研究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