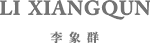李象群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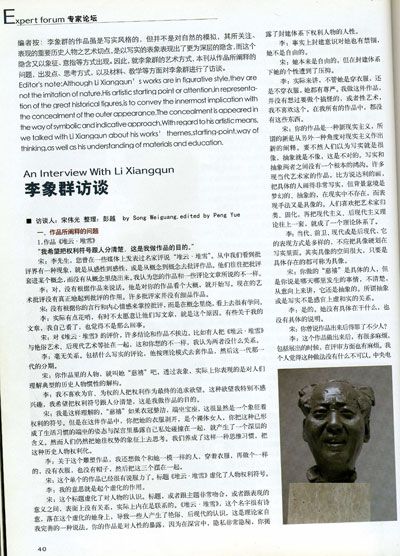 访谈人:宋伟光 整理:彭越
访谈人:宋伟光 整理:彭越 一、作品所阐释的问题
1.作品《堆云·堆雪》
“我希望把权利符号跟人分清楚,这是我做作品的目的。”
宋:李先生,您曾在一些媒体上发表过名家评说“堆云?堆雪”。从中我们看到批评界有一种现象,就是从感性到感性,或是从概念到概念去批评作品。他们往往把批评套进某个概念,而没有从概念里绕出来。我认为您的作品和一些评论文章所说的不一样。
李:对,没有根据作品来说话。他是对你的作品看个大概,就开始写。现在的艺术批评没有真正地起到批评的作用。许多批评家并没有细品作品。
宋:没有根据你的言行和内心情感来掌控批评,而是在概念里绕,看上去很有学问。
李:实际有点花哨,有时不太愿意让他们写文章,就是这个原因。有些关于我的文章,我自己看了,也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宋:对《堆云·堆雪》的评价,许多结论和作品不挨边。比如有人把《堆云?堆雪》与艳俗艺术、后现代艺术等扯在一起,这和你想的不一样,我认为两者没什么关系。

李:毫无关系。包括什么写实的评论,他按理论模式去套作品,然后这一代那一代的分期。
宋:你作品里的人物,就叫她“慈禧”吧,透过表象,实际上你表现的是对人们理解典型的历史人物惯性的解构。
李:我不喜欢为官、为权的人把权利作为最终的追求欲望。这种欲望我特别不感兴趣,我希望把权利符号跟人分清楚,这是我做作品的目的。
宋:我是这样理解的,“慈禧”如果衣冠整洁,端坐宝座,这很显然是一个象征着权利的符号。但是在这件作品中,你把她的衣服剥开,是个裸体女人,你把这种已形成了生活习惯的端坐的姿态与深宫里暴露自己私处碰撞在一起,就产生了一个深层的含义。然而人们仍然把她往权势的象征上去思考。我们养成了这样一种思维习惯,把这种历史人物权利化。
李:关于这个雕塑作品,我还想做个和她一模一样的人,穿着衣服,再做个一样的,没有衣服,也没有帽子,然后把这三个摆在一起。
宋:这个单个的作品已经很有说服力了。标题《堆云?堆雪》虚化了人物权利符号。
李:我的意思就是起个虚化的作用。
宋:这个标题虚化了对人物的认识。标题,或者跟主题非常吻合,或者跟表现的意义之间,表面上没有关系,实际上内在是联系的。《堆云·堆雪》,这个名字很有诗意,落在这个虚化的她身上,导致一些人产生了艳俗、后现代的认识,这是理论家自我完善的一种说法。你的作品是对人性的暴露,因为在深宫中,隐私非常隐秘,你揭露了封建体系下权利人物的人性。
李:事实上封建意识对她也有禁锢,她不是自由的。
宋:她本来是自由的,但在封建体系下她的个性遭到了压抑。
李:实际来讲,不管她是穿衣服,还是不穿衣服,她都有尊严。我做这件作品,并没有想过要做个搞怪的,或者性艺术,我不喜欢这个。在我所有的作品中,都没有这些东西。
宋:你的作品是一种新现实主义,所谓的新是从另外一种角度对现实主义作出新的阐释。要不然人们以为写实就是很像,抽象就是不像,这是不对的。写实和抽象两者之间没有一个根本的鸿沟。许多现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比方说达利的画,把具体的人画得非常写实,但背景意境是梦幻的、抽象的,在现实中不存在,而表现手法又是具像的。人们喜欢把艺术家归类、固化,再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往上一套,就成了一个理论体系了。
李:当代、前卫、现代或是后现代,它的表现方式是多样的,不应把具像硬划在写实里面。其实具像的空间很大,只要是具体存在的都可称为具像。
宋:你做的“慈禧”是具体的人,但是你说是哪天哪里发生的事情,不清楚,从意向上来讲,它还是抽象的。所谓抽象或是写实不是感官上虚和实的关系。
李:是的。她没有具体在干什么,也没有具体的说明。
宋:你曾说作品出来后得罪了不少人?
李:这个作品做出来后,有很多麻烦,包括展出的时候,在评审方面也有麻烦。我个人觉得这种做法没有什么不可以。中央电视台制作了一个新闻栏目,叫“讲百姓的故事”系列,最近播出了“798的故事”,播放了我在做这个作品,那都能播,这里展览为什么不可以呢?老百姓对艺术品的认识,往往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而不是把它作为艺术品来看。我们不能把艺术品当成像电影中的场景那样真实的东西来看,因为艺术的东西做出来是虚的,艺术家想做的是提出来一些问题,或者说明一些问题,我并没有要给他一个什么定义。
2.作品毛泽东、郭沫若、八路军、徐悲鸿像
“不是我把‘毛泽东’放那么高,而是我们把他放那么高”
宋:人们对作品的解读进入一种误区。讨论这个作品播放不播放,展览不展览,这是很无聊的事情。实际上你是想突破一种对所谓具像雕塑认识的禁锢,对固有理解的突破。你对历史中典型人物的理解进行了解读,这促使你做了一系列作品。比如前几年的《郭沫若》,就是很典型的突破尝试。
李:我总想在肖像里面有所突破,但每走一步都受到质疑,受到非议。我做《我们走在大路上》,本来下面有一个台柱,后被人拿走了。台柱用很漂亮的不锈钢做的,很高。来工作室的人都说,你怎么把“毛泽东”放那么高的台柱上?我不禁问:是我放那么高吗?实际不是我把“毛泽东”放那么高,而是我们把他放那么高。本来是我们在大路上走,您把他放那么高的柱体上,是纪念碑式的柱体,而我是想把延安时期那种土八路的真实感觉做出来,成为一个普通的人。
宋:有必要把人物放在那个高高的纪念碑上吗?
李:其实是没必要。这就有问题了,问题是回头看历史,有许多人指责他,认为是他自己走到这么高的位置上来。其实没有必要指责他,是我们把他放到这上面来的。责任是谁的呢?人们就是没考虑过自己的责任。
宋:你的意图是打算把他放在平地上,还是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呢?
李:我想把他放在平地上,而事实上在概念中已经把他放在“高台”上了
宋:《我们走在大路上》是纪念碑式的。你本来的出发点是认为毛泽东和普通人一样在走着,但是我们把他放在一个高台上,意义就不一样了,纪念碑的意义就在于那个基座,把人放下来就不是纪念碑了。
李:好像是他自己走上去的,其实是我们把他放上去的。
宋:在我们的固有意识中,毛泽东必须站在上面。
李:我和一些老先生也聊到过不同时期做的毛泽东像,老先生们自己做毛泽东像时,也容易每次就做出那个时期的,伟人的毛泽东像,这是一种固有的看法。
宋:你做的这些肖像,改变了做伟人的既定的模态,你想把伟人做成普通人,强调人性。没有高台子的走在大路上就让人感到很亲切了,并不是一个领袖挥手向前的样子,这是你做的东西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郭沫若》也是这样,他那个眼睛,你把他处理成一个片状。
李:当时他的家属也因为这个不愉快。
宋:你的作品《毛泽东》《慈禧》,还有《郭沫若》,透过其表象看,不是写实,也不是具像,你有你自己的解读语言。我认为这就是现实主义,所谓高于生活。理论家、评论家不应该给你来定性什么,不是用概念套概念,用符号套符号。
李:有时候我也羡慕一些理论家,因为不管怎么样,他们是为自己打工,但是有一点,他们真正的人性释放不了,这也是挺悲哀的。我觉得慈禧也好,毛泽东也好,作为一个人物,我想他们都有被禁锢的一面。我跟邓林(邓小平之女)聊天的时候,她说父亲退休后想上街逛逛商店,但是做不到,这是一种悲哀。就算到商店去了,也是先戒严,就他一人在那走,他也不自由。我们可能比他们要享受更多的自由。
宋:我看过很多毛泽东的传记,国外人写的,从领袖身份到普通人,对这个过程他们往往阐述得比较客观。在政治上他对党派是毫不留情的,但是你跟他私交,他很亲切。
李:他其实很有艺术家的特质。我看了不少他的照片,有一张是他在寺院里,在地上铺一张席子,正准备躺下睡觉,这个画面特别棒。还有一张是他在湖南考察,把裤腿卷起来,满脚泥,坐在凳子上抽烟。
宋:你的作品体现了最本源的东西,一句话就是人性,你恢复了他们人性的本来面貌。
李:我就想敞开来说点真话。做作品应该要真诚。我不太喜欢虚伪,做人不能虚伪,做作品也不能虚伪,要真实,要自己喜欢。有些艺术是给别人看的,但是我的作品首先要给自己看,至少我要自己喜欢。我也给别人看,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喜欢,所以我很真诚。
宋:我看你把握毛泽东也好,慈禧也好,神态都不一样。毛泽东雕塑他的眼神很锋利,但是又很世人化。你表现的不是模式化的人物,好像是生活中一刹那的显现。
李:一个人一瞬间可能流露出他的真实,尽管他真实的状态可能很少表露。什么是真实,抓到他那种精神上的东西,把它给挖掘出来。
宋:你工作室里还有一些小的人物雕塑,那也是一些领导人吧。做那个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李:对,那个雕塑里面雕了九大元帅,都是八路军,里面没有陈毅,陈毅是新四军。是山西来找我做,一共塑造了11个人,里面多了个左权和邓小平。当时我的想法是不太愿意把人一字排开,那太像照片,这个场面是在散会间大家在休息,有正着站的,有侧着的,有笑的,有不笑的,我就想做一些特别朴实的八路军。
宋:跟你现在做的思路不太一样,不是纯独立的,自我化的创作。
李:对。像这种个人独立创作的人物,或不是独立创作的,我还是尽量走自己创作的那个方向。我说过,找我做作品,我就做我自己看到的,尽量反映它的真实性。
宋:基本上你这几年一直是这样过来的,是吧?
李:对,正经这样开始做,是从上世纪90年代做《巴金像》开始的。我还有件作品《茅盾》,给上海做的,那边说用自己的风格、表现语言来做人物。
宋:工作室里面还放了《徐悲鸿》。做《徐悲鸿》你是怎么考虑的?
李:我看了许多照片,他都是眯着眼睛看东西,但我这个雕塑里他睁开眼睛。他很少有这样的状态,偶尔睁一下眼睛看。我们也是搞画画的,也有这种情况,就是看某个东西时,突然一闪念,眼睛一亮。这个《徐悲鸿》手里没拿笔,但他的手是握笔的手势,另一只手背着。他看到某个东西特别有意思时,就下意识做出握笔的手势。
宋:人物作品毛泽东谈了,慈禧谈了,刚才又谈了徐悲鸿,还有八路军,还有什么?
李:还有个胸像,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清华那里放着,刚做完,包括我现在做的人体、胸像都带有一点场景。过去,我们为了做人体而做人体,为了做习作而做习作。习作的概念是研究和实践。我就想把这种研究和实验由原来纯粹的架上式的转换成场景式的。我现在就想做人体和场景之间的关系,这个模特是我所看到的一种环境下的模特。包括人物的衣服所放的位置,坐的那个椅子,靠背上压的褶皱都要做出来。
宋:做亲眼看到的东西。
李:对,而不做过去的一种模式。还有像毛泽东、慈禧这样的历史人物不是玩物,不是让你随便把玩的东西。其实包括对毛泽东的认识也是这样。有些人做毛泽东像又是穿花衣服,又是青眼獠牙,其实都不好。即使他不是供奉的神,对于一个人的人格的起码尊敬,这样做也不行。对于包括慈禧在内的历史人物雕塑,我的作品里绝没有一点贬义。
宋:我能看出来没有,你完全是一个对人性的解读。
李:对,因为我做《堆云·堆雪》的时候,我在想她这个人应该特别美,我做她处于最美的年龄段上,是心理最漂亮的时候,并且很中国化的一个形象。
宋:你心里没有想得那么多,想那么多是搞理论的人自己想的。
二、做肖像雕塑的出发点
“就是还原,还原人的真诚、真实、朴素”
宋:做毛泽东、郭沫若、慈禧等,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李:就是还原,还原人的真诚、真实、朴素。我记得很小的时候,看普希金的诗,里边说到自然的元素包括哪些,我觉得人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我就把人还原成大自然。
宋:你把历史上典型的人物用一种还原的方式来表现,而不是把他固化在已有的模式中,伟人必须是怎样的。
李:把符号明确化、符号化的人让人感觉到一种分离。
宋:体现符号,但不是符号化。
李:让人们意识到摘掉符号后是一种什么概念,放在上面又是一种什么概念,这是特别重要的。
宋:这使我想起卡西尔的一句话:“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动物。”那么可以推理人的精神产品——艺术,便是符号的语言。
李:是的,我们看人物的时候,喜欢联系他的身份一起来看。为什么要通过做这些典型人物来提出这些问题呢?因为这些人的身份是大家熟知的。
宋:你的想法把过去那种对他们的看法消解了。今天我们谈到把人物本源化,而且用符号这个概念,把符号装在他身上是什么,把符号分离出来又是什么,这非常重要。
李:举个例子,人到60岁退休,在退休之前是这样或那样的身份,这时候你发现人们对你前呼后拥,但一到退休以后,门庭就冷落了,有些人感到特别失落,因为符号没有了,给剥离出去了,所以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还是作艺术家好,没有符号,他凭自己的双手来创造自己。我做雕塑无所谓是哪个派,这个没关系,我从来不考虑这些问题。我一直沿用我自己的思路。
三、思考方式
“要了解自己就要把魂从身上拿出来,反过来再看自己”
宋:没有个人理解的艺术家我认为不是真正的艺术家。再就是一些作品形状千千万万,但精神没变,这不是创意,精神变了,才是创意。前一阵我看了一件作品,是把宋代郭熙的山水画做成玻璃片,再把玻璃片交错放在博物馆式的玻璃盒子里,他说这就是创意。有名的理论家给他策划做展览,我认为这是玩了个新花样,没有任何创意,把山水画用这种方式重新组装,从视觉上的经验来看这依然是山水画。
李:这只是一种材料的变化。更重要的还是在人文层面上再更深层次地去挖掘,要把作品作为一种重新解读和看待问题的方式。我在教学中也经常跟学生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我们要从自己站着的原点把自己拉出来,再看我们这个位置,这样才能看得比较透彻。其实每个人不太容易了解自己,要了解自己就要把魂从身上拿出来,反过来再看自己。这可能很有意思,就像你看别人一样看得清楚,就像宇航员在太空中看地球。
宋:这种说法在明代就已经有了,叫“倩女离魂”。这种思考方式对我们搞创作特别有用,你自己不是你自己,但是你又还是你,若即若离的状态。
李:我参加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艺术工程会议,在会议中我讲,对一些艺术作品,尤其是对人物肖像这块,我们要离开自己,离开我们要做的东西来看。假如说我们跳到未来的500年,回过头来看今天我们所做的东西,作品是不是可信的?是不是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思想?你做得可信,这不是概念的,人们看了以后觉得真切可信,这种可信可能是情感的真切,不一定要是形式的可信。当人们看到你的作品时,能为之一动,这实际上就够了,如果连动都动不起来,那就什么也没有了。
宋:他自己好像在动,实际上他没有动,他自己也不激动。他用概念玩个花样,他那么激动,那是假激动。
李:他自己并不喜欢。哭是假哭,笑是假笑。做雕塑要跳出来看,比如做人体,要把人的眼睛、鼻子、嘴、耳朵看成是单个的物体,而不是你所熟悉的人体的一部分。要保持头脑清醒。像医生做解剖,不会考虑这是不是人体,而是把人体结构中的肢体看成是整体里的一个物体来解剖。做雕塑做的不是人体,做的是物体,等你把这些不同的物体组合起来后,才发现你做的是人体雕塑。应该是这样一种观察和做作品的方式,不能掉进去看。我看一些学生做的作品,我说你做的不是人体,而是裸体。
四、对教学以及对材料的认识
“找着规律了,做的东西就对了”
“就他那块布,就到位了”
宋:请您再谈一下您的教学体会以及对材料的认识。
李:我教学生要学会找规律,规律找到了,技法,材料就不是问题了。找着规律了,做的东西就对了。在做作品当中,我也在思考问题。所以说教创作课难嘛,就是你不能替代所有人去为他们思考。你只能去让他尽量多地接触问题,教他去跟当下的生活和问题贴近,其实作品就是思考问题。教创作课只能跟他们提一些创作之外的东西。我们系里面,我的研究生,有的要做行为艺术,我说可以去做。有人就问,那也算是雕塑吗?我说当然算,他通过自身的身体语言去占有空间形成一种艺术状态,也是艺术。谈到材料,上世纪90年代用不锈钢做了很多城市雕塑,到处都是,做得很粗糙。
宋:现在喷漆也差不多泛滥了。
李:其实喷漆也好,不锈钢也好,我们现在批评那些粗糙的雕塑,不是因为喷漆和不锈钢不好,其实材料本身用好了也是决定作品好坏关键的一部分。材料也是观念的一部分,比如马蒂斯做的那个舞蹈的女孩雕塑,他用真的布来做她的裙子,如果用铜来做,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你用什么材料都不行,就他那块布,就到位了。有些东西就是这样,跟你要表达的主题要绝对贴切。
宋:现在有些作品照着原型假山石,再用不锈钢敲出个假山石。便以为把一种材料转换为另外的材料,这就是作品的转换。这不一定,首先你要对材料有精神性的认识,为什么人们把紫砂壶捧在手里呢,因为它的材料跟身体是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法国葡萄酒要放在玻璃杯子里呢,你不可能把葡萄酒放到小泥壶里面去,这就是材料的特性。
李:这是材料本身起的作用。它反映给观众一种视觉反映。
宋:或者叫视觉心理吧。就是你在做什么样的思考,而不是做什么作品。
五、对学科分类的看法
“分为平面和立体”
宋:谈到这里,自然牵扯到学科的分类。
李:我不止一次说过,美术院校对学科的分类是错误的。有些学院分设计和造型,难道设计不是造型吗?造型就没有设计吗?这是个问题也不是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分为平面和立体。平面和立体可以相互补充,学科之间要互相找联系。比如服装是立体类造型,而它又需要找平面类的染织学科知识,雕塑和绘画也需要互助,互相找有利的帮助。立体和平面都可以归到视觉下面。画家好做,雕塑家也好做,艺术家不好做。因为艺术家需要的不只是专家,而是要博学多才,学识宽广。
宋:对,因为广博也是精深的基础。
六、对您的学术评价
“像我这类型,不是王朔们”
宋:你除了做作品之外,还要通过媒体来发布文章和信息,在商业性一点的杂志发表也好,这有卖点。如果从学术上谈,对于你的学术评价,我认为和你的本意相差很远,乃至不能够让人们正确认识你,或是体会到你作品的深度。
李:这是因为根本没有透彻地跟我谈过。
宋:要不然在文章中开始吹捧。吹捧往往容易遭到攻击,这种攻击是名利人身攻击,而不是学术上的辩论。
李:对。我看了一些关于我的文章,其实心里挺难受。后来我就不看了,网上什么都有,要看下去,谁也甭活了。后来我不再上网,因为我不想再看,很多人对作品不理解。
宋:你的学术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而媒体的报道失真,甚至歪曲,没有把你的作品当成学术来思考。
李:我是这么认为我自己的,像我这类型,不是王朔们,我也不太喜欢痞子文化。我想实实在在地做研究。现在有种风气,好像你越痞,越匪,越当代。
宋:今天您谈了好几点,对做历史人物雕塑的想法,对材料的认识,还有教学等几方面,谈的面比较广。
李:很宽泛,艺术本身就很宽,它所触及的领域很宽,这种采访方式也不累。
宋:所以我从来没把雕塑只当成雕塑看,而是要从大文化角度来看雕塑。时间限制,不得不结束我们的访谈,谢谢您!
李:感谢!